空杯
by康书白
行驶在蓝田汤峪野猪窝盘山道上颠簸,我的心绪也跟着起伏不定。此行不为别的,只为拜访一位易学家,作家——灵遁者。车窗外重峦叠嶂,苍翠深浓,风一吹,就好像山在向你招手。与灵遁者相识,是通过他的作品,但从未见面,此次路过西安,正好有时间。

车子停在一处朴素的院前,这个院子坐落在半山腰,院子连门都没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墙正中的高墙上,有一只“眼睛”状的图案,然后是一些简介内容,但我并没咨询看,灵遁者便迎了上来。那只LOGO眼睛仿佛注视着每一个路过的人,注视着周围的山。
进门细问,才知道这个“眼睛”LOGO的灵感来源于八卦。第一眼见灵遁者本人,他身形并不胖,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却毫无想象中隐士的孤绝之气。寒暄几句,那声音爽朗有力,没有惊涛,也无深谷回音——如不紧不慢的流淌。
进入屋内,是那种特别“旧”的感觉,因为都能看见光从屋顶的缝隙射进来,这不是典型的“漏风”吗?不过屋顶很高,大概有三层楼那么高,灵遁者介绍说,这边的老房子都是这样的结构。和陕北的窑洞一样,冬暖夏凉。

我没有去过陕北,自然无法体会他说的窑洞是怎么样的?不过进屋子确实能感觉到凉意袭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屋子的四周都挂着灵遁者的油画。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油画作品,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说不出他要表达什么,但似乎我确实被吸引住了。
看了几分钟,灵遁者招呼我们喝茶。我们随行4人,围坐在院子的玻璃桌子上,桌子也很简单,这种玻璃一看就是那种双层隔音玻璃,而桌子的腿,就直接是轮胎。同行的朋友,恰好有一个是做玻璃生意的,我们打趣道:“你回去也可以这么弄,学会了吗?”
我朋友笑着说:“还真没有这样试过。”灵遁者跑进跑出,烧水,坐下,从容布茶。大家问了好多问题,比如秦岭多大?这样的山多吗?这租金多少?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这方寸茶席很快成了大家高谈阔论的舞台。
后来聊到高兴处,你引一段佛经,我谈一通老庄,他论及当下社会种种,言辞激烈处几乎要撞翻手边的茶盏。人人争相倾吐自以为是的“洞见”,生怕被旁人抢了话头。
唯独灵遁者,始终在沸水将尽时默默添续,在众人争辩的缝隙里安静地将茶汤注入一只只空杯。有人慷慨激昂,他便轻轻点头;有人语塞沉吟,他便适时递上一句“嗯,是这样”或“有道理”,言语轻巧如一片茶叶坠入水中,不惊波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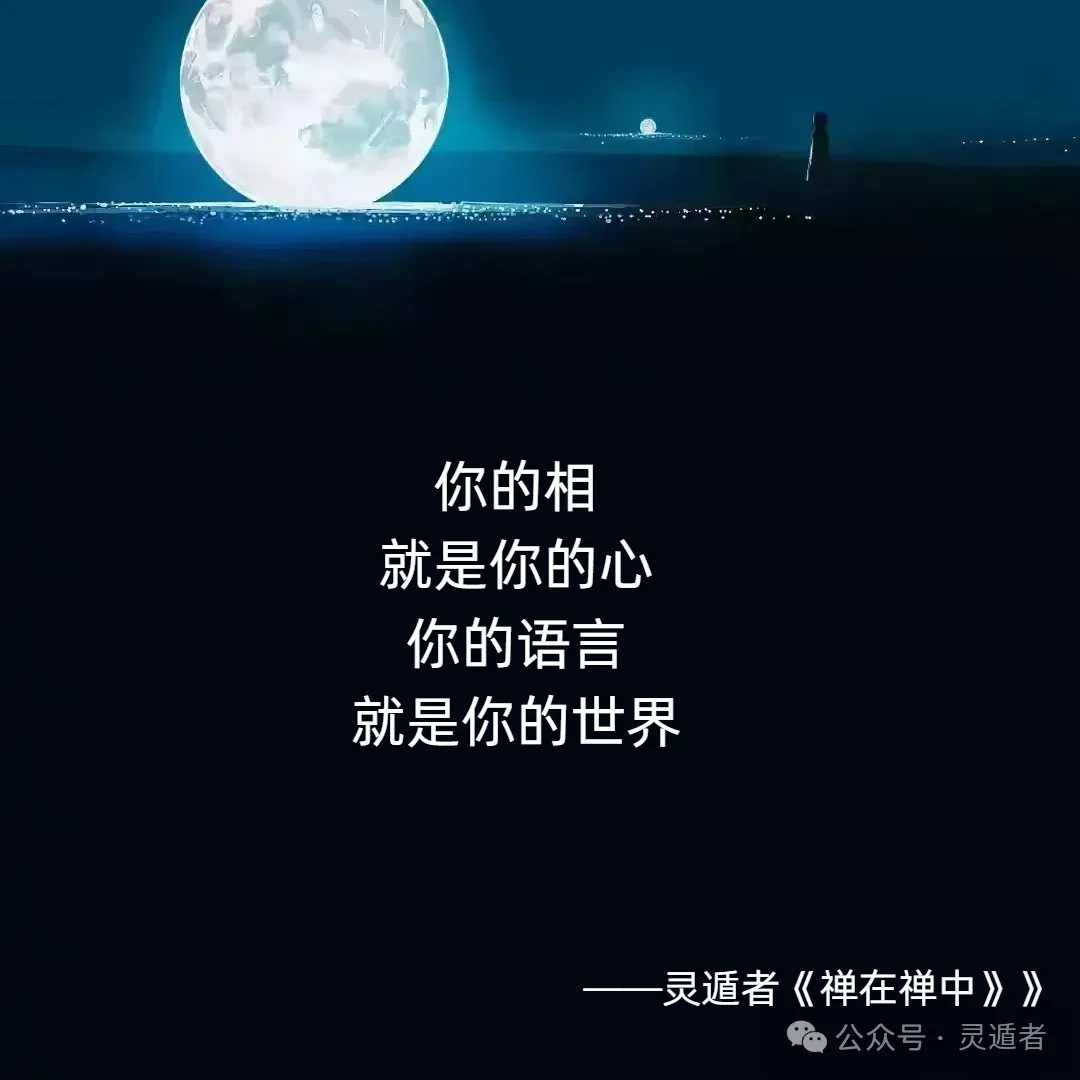
他眼含笑意,不时扶一下眼镜,目光在每一张涨红的脸上静静停留,如同老师凝视学生——那眼神里盛的不是评判,竟是纯粹的聆听,仿佛我们口中那些浮夸的道理,经由这山间水汽浸润,竟也值得包容。
不知不觉,已经2个多小时过去了,茶喝尽了,舌燥了,太阳下山,人也倦了,我自己也打了哈欠,这和我们旅途劳顿有关。一行人便终于起身告辞。灵遁者送至旁边的小院,依旧是那副温和神情,挥手作别,如送别寻常老友。
下山的路被暮色浸染。我坐在归程的车里,起初大家觉得心满意足,仿佛刚才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论道。然而当城市的灯火在车窗处浮起时,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落感却悄然袭上心头。车窗映出自己模糊的脸,我突然惊觉:自始至终,灵遁者未曾主动说过一句“高见”,未曾试图教导过任何人!那些我们引以为傲的滔滔雄辩,在他面前,竟如同对着深谷呼喊,只听见自己激越的回声。
我本来想着问几个问题,竟然也一个也没有问,都不知道讨论了什么。可能话题,始终一下子左,一下子右。而且有些话,我也不方便问。
刚才喝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记起灵遁者那双眼睛——当大家争相倾倒心中块垒时,那双眼睛始终清亮而专注,如深山古井,波澜不惊,却又分明映照出每一个说话者沉醉于自我表达时的姿态。那不是赞同,不是敷衍,更不是漠然。那是一种更深沉的容纳与承托,容纳所有喧哗,承托一切浮浅,如同大地无声承载万物生长。

车驶入喧嚣市区,西安和北京一样堵车。深夜,回到酒店的房间,望着眼前空空的茶杯,我打了个寒噤:我们自以为追寻着高人,渴求着点拨与开示,却原来自己才是那喧嚣的源头。
打扰了自己,也打扰了别人。灵遁者端坐于终南深处,不言不教,只是递过一杯清茶,予人一方静默如山的倾听。他早已将“道”化入那寻常的举止与无言的容纳之中——我们执迷于杯中寻琼浆,却忘了最深的滋味,恰是那只空杯的容量与无言。
我拿起手机犹豫了下,还是给灵遁者老师发了信息:“我们刚回到酒店,今天叨扰了。”

不一会老师回复:“客气了,下次路过再来。”
本文转载自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