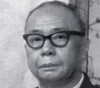近现代中国画批评状况及其得失https://www.huajia.cc 2009.05.31 10:36 来源:文汇报 发表评论(0)
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是那个特殊年代美术研究与批评的重要特征,在对艺术表现的理解上,以普通民众理解与否作为区分艺术阶级性的标准,故推崇现实主义,徐悲鸿  所倡导的艺术主张因而也受到了极高礼遇。这种片面化的理解发展到1960年代,终于出现了文艺只能表现建国后十三年的极端主张,甚至全面批判被“死人”和“洋人”统治的艺术,直到改革开放后,江丰还将表现现实题材的人物画之外的山水、花鸟画尽数斥为“行货”……这就使得旨在抒情畅神的文人画与以尚变形、抽象的西方现代艺术,一度成为反动、腐朽的代名词,一批老画家和留洋画家,因之几乎放弃创作。并且当时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形成的教条化理解,也深深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理论研究。 所倡导的艺术主张因而也受到了极高礼遇。这种片面化的理解发展到1960年代,终于出现了文艺只能表现建国后十三年的极端主张,甚至全面批判被“死人”和“洋人”统治的艺术,直到改革开放后,江丰还将表现现实题材的人物画之外的山水、花鸟画尽数斥为“行货”……这就使得旨在抒情畅神的文人画与以尚变形、抽象的西方现代艺术,一度成为反动、腐朽的代名词,一批老画家和留洋画家,因之几乎放弃创作。并且当时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形成的教条化理解,也深深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理论研究。尽管有面目单一之弊,但1950年代以还强调现实主义、反映时势的中国画艺术,凭借从美协到全国美展的制度保障,毕竟造就出了大批优秀艺术家与作品,如蒋兆和  、傅抱石 、傅抱石 、石鲁 、石鲁 、赵望云 、赵望云 、李可染 、李可染 、黄胄 、黄胄 、唐云 、唐云 、应野平、钱松喦 、应野平、钱松喦 、宋文治 、宋文治 、关山月 、关山月 、方增先 、方增先 、周思聪 、周思聪 、周昌谷 、周昌谷 ……皆属其中有代表性的大家,其作品亦成为中国现代画史上的经典。所惜这一局面仅持续了十多年,“文革”的爆发终令一度轰轰烈烈的“新中国画”运动趋于夭折。 ……皆属其中有代表性的大家,其作品亦成为中国现代画史上的经典。所惜这一局面仅持续了十多年,“文革”的爆发终令一度轰轰烈烈的“新中国画”运动趋于夭折。然而“服务于崇高的目的”未必一定创造伟大的艺术,“服务于闲散的心情”也未必不能催生伟大的艺术,虽然极“左”文艺路线将中国艺术引入了万马齐喑的时期,但如谢稚柳  、黄秋园 、黄秋园 等漫写性灵的老画家,和由原先的积极进取转向欲说还休的石鲁 等漫写性灵的老画家,和由原先的积极进取转向欲说还休的石鲁 、陈子 、陈子 庄等新时期画家,却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用自己的画笔阐说了传统文人画“欲辩无言”的深刻含义。 庄等新时期画家,却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用自己的画笔阐说了传统文人画“欲辩无言”的深刻含义。正所谓矫枉过正、物极必反,当“解放思想”运动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引发了艺术家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大逆反。1980年代,在西方现代艺术诸如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流派的影响下,画家开始打破以往唯写实主义是从的观念,进而更出现了将之视作没落方向  的倾向,林风眠 的倾向,林风眠 等一批画家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极高评价。而在传统绘画领域,非但出现了“新文人画”运动,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人们也开始将不求形似的文人画视作中国画的高品。 等一批画家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极高评价。而在传统绘画领域,非但出现了“新文人画”运动,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人们也开始将不求形似的文人画视作中国画的高品。文人大写意能不能代表中国画的全部 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画的格局是以明清大写意与元代小写意、唐宋严谨画风的先后兴盛而呈三足鼎立,那么1980年代的学术界,最初是将文人大写意视作为中国画的杰出代表。郎绍君“二十世纪传统四大家”观点的提出,是这一转变最具代表性的体现。 郎氏肯定吴昌硕  、齐白石 、齐白石 、黄宾虹 、黄宾虹 、潘天寿 、潘天寿 这四家的成就,诚然准确,并且他提出近现代画史上中西合璧派与传统派的并存,立论精当,其说影响广泛因而顺理成章。然而,他认为上述四家代表了整个二十世纪传统中国画的成就,其实并不全面。严格地说,这四家应定义为“传统金石写意”四大家,否则,非但漠视了以张大千 这四家的成就,诚然准确,并且他提出近现代画史上中西合璧派与传统派的并存,立论精当,其说影响广泛因而顺理成章。然而,他认为上述四家代表了整个二十世纪传统中国画的成就,其实并不全面。严格地说,这四家应定义为“传统金石写意”四大家,否则,非但漠视了以张大千 等为代表的另一支取法唐宋的重要的传统力量,而且对以傅抱石 等为代表的另一支取法唐宋的重要的传统力量,而且对以傅抱石 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亦有回避之嫌。这一观点,或许是作者对建国后中国画刻意强调主题创作抱有不同见解,而且与1950年代以来大陆国画界潜在的思维定势颇为相关。 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亦有回避之嫌。这一观点,或许是作者对建国后中国画刻意强调主题创作抱有不同见解,而且与1950年代以来大陆国画界潜在的思维定势颇为相关。需要说明的是,独尊文人写意画的思潮在进入新世纪后同样遭遇了物极必反,徐建融  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郎绍君等相左的意见,鼓吹以工致深入见长的宋元画风,并激烈地批评明清文人写意画。徐的观点亦引起了很大争议,然而指出文人大写意不能代表中国画的全部,却是其说的价值所在。 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郎绍君等相左的意见,鼓吹以工致深入见长的宋元画风,并激烈地批评明清文人写意画。徐的观点亦引起了很大争议,然而指出文人大写意不能代表中国画的全部,却是其说的价值所在。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另一大表现,乃是李小山“中国画穷途末路”说的提出。其立论根据是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乃封建社会产物,在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代,必然失去发展空间。缘此,一些学者也推导出中国画必须通融西方现代艺术而进入“现代”的理论,一时间此种学说开始广为人们接受。 李的观点,对打破极“左”思想禁锢与接受西方现代艺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致命的问题,是延用了长期盛行的简单化的阶级斗争方法,也即前述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教条化理解。依此类推,非但中国诗画、戏剧等所谓“四旧”,而且中国传统工艺如筷子、食品,都恐因其“封建性”而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准此,中国画也势必被西方现代艺术所取代,传统艺术只剩下为西方文艺增添地域性文化元素的价值(此种隐患目前仍广泛地存在于包括当代绘画、影视在内的文艺界)。这一观念,事实上与江丰当年从世界性的角度主张以油画取代中国画,出于同一逻辑。“左”的思想多年的影响,已造成人们的日用而不知,当时有学者提出潘天寿  是“没有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之说,同样也属此种观念的延伸。中国画的“现代”之说,是在振奋人心的1980年代提出,但却不可避免地沾溉了此前理想化、“大跃进”式的“赶英超美”习气。 是“没有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之说,同样也属此种观念的延伸。中国画的“现代”之说,是在振奋人心的1980年代提出,但却不可避免地沾溉了此前理想化、“大跃进”式的“赶英超美”习气。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又一大表现乃是吴冠中  倡导“形式美”,此说是对建国后文艺界唯“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定律是从,美术界定写实于一尊的物极必反。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整个绘画界掀起了崇尚形式表现与抽象审美的热潮,声势至今浩大。事实上真正奠定吴冠中 倡导“形式美”,此说是对建国后文艺界唯“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定律是从,美术界定写实于一尊的物极必反。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整个绘画界掀起了崇尚形式表现与抽象审美的热潮,声势至今浩大。事实上真正奠定吴冠中 学术地位的,正是他对形式主义审美的倡导与实践,而非是其成名后被热炒的“笔墨等于零”。1990年代,卢辅圣 学术地位的,正是他对形式主义审美的倡导与实践,而非是其成名后被热炒的“笔墨等于零”。1990年代,卢辅圣 在上海书画出版社组织董其昌、四王、赵孟頫 在上海书画出版社组织董其昌、四王、赵孟頫 \\等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从笔墨形式的角度重新认识古人,影响巨大。这既是对当年武断批判文人画的反拨,也令董其昌、四王、赵孟頫 \\等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从笔墨形式的角度重新认识古人,影响巨大。这既是对当年武断批判文人画的反拨,也令董其昌、四王、赵孟頫 \\的绘画,自此不再成为罪恶,同时也恰恰是形式主义美学渗透入中国画史论研究的表现。 \\的绘画,自此不再成为罪恶,同时也恰恰是形式主义美学渗透入中国画史论研究的表现。至于吴冠中  的“笔墨等于零”,其实只是西画出身的他对自己宣纸彩墨画创作缺乏笔墨修为的一种曲意辩护,在学术上并无价值,当然对新闻媒体,这又当别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两种不同笔墨系统”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吴氏申辩的学术化表述。其说的核心,与一度兴起的“现代水墨”在观念上甚近,即认为只要用水墨、宣纸,而无论是否学过中国画,画出的同样是笔墨。此说只承认笔墨的表相,而否认笔墨的内涵,实质是认为“非笔墨”也是“笔墨”的一种。然而依此类推,中国民间自古有用油漆描绘、装饰器物的传统,国人是否因此能与欧洲人同享油画的发明权?绘画的笔墨,实际上只能是指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舍此再无其他。概念有内涵、外延之分,以外延混淆内涵,或者说“白马非马”,固是智慧,但毕竟多被用作辩术。在现实中,我们不会因为人与鸡都长毛,就承认人等于鸡,或者将“不是人”当作“人”的一种。当然“现代水墨”的主张并非是为吴冠中 的“笔墨等于零”,其实只是西画出身的他对自己宣纸彩墨画创作缺乏笔墨修为的一种曲意辩护,在学术上并无价值,当然对新闻媒体,这又当别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两种不同笔墨系统”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吴氏申辩的学术化表述。其说的核心,与一度兴起的“现代水墨”在观念上甚近,即认为只要用水墨、宣纸,而无论是否学过中国画,画出的同样是笔墨。此说只承认笔墨的表相,而否认笔墨的内涵,实质是认为“非笔墨”也是“笔墨”的一种。然而依此类推,中国民间自古有用油漆描绘、装饰器物的传统,国人是否因此能与欧洲人同享油画的发明权?绘画的笔墨,实际上只能是指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舍此再无其他。概念有内涵、外延之分,以外延混淆内涵,或者说“白马非马”,固是智慧,但毕竟多被用作辩术。在现实中,我们不会因为人与鸡都长毛,就承认人等于鸡,或者将“不是人”当作“人”的一种。当然“现代水墨”的主张并非是为吴冠中 辩护,而是旨在借水墨画的民族特色,为中国现代艺术谋取其于国际主流艺术圈的一席之地。因而此种学说,非但同样带有鲜明的“大跃进”色彩,而且更脱离了艺术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诉求。 辩护,而是旨在借水墨画的民族特色,为中国现代艺术谋取其于国际主流艺术圈的一席之地。因而此种学说,非但同样带有鲜明的“大跃进”色彩,而且更脱离了艺术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诉求。文艺中心北移对艺术评判标准的影响 近现代画史的一大变化乃是以1950年代为转折,中国文艺的中心由南方转向北方。建国前京津与广州地区虽亦是重镇,但以上海为核心的江南画苑却是当时整个中国画坛的中心。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吸引了各地优秀画家来此谋生,吸收了海外艺术丰富的养料,从而形成了文艺高地。建国后北方文艺所以日益兴盛,主要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  及其配套体制,决定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同时也成为文化中心。缘此,身居北京的画家被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力量推向潮头,其中年长望重者如齐白石 及其配套体制,决定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同时也成为文化中心。缘此,身居北京的画家被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力量推向潮头,其中年长望重者如齐白石 ,更成为冠绝于时的权威,甚至当年批评其艺术者,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齐氏所擅长的画风及其艺术师承,成为建国后中国画家与研究者最为重视的内容,也使得民国时称名的张大千 ,更成为冠绝于时的权威,甚至当年批评其艺术者,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齐氏所擅长的画风及其艺术师承,成为建国后中国画家与研究者最为重视的内容,也使得民国时称名的张大千 、吴湖帆 、吴湖帆 ,以及在北京盛极一时的金城画系,因种种原因而被视为“保守派”,直到陆俨少 ,以及在北京盛极一时的金城画系,因种种原因而被视为“保守派”,直到陆俨少 受潘天寿 受潘天寿 之聘执浙美教席,才令此种情况在江南稍作改观。 之聘执浙美教席,才令此种情况在江南稍作改观。由于大写意的兴盛,工致深入的双钩与水墨表现技法在建国后的中国画领域相对处于弱势。至1980年代,作为建国前金城画系的余绪,北方一些画家提出了“工笔重彩”的概念并成立了专业协会,这一举措,显然也带有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自我保护色彩。然而正是本意良善的这一举措,却造成了学术的误读:“工笔重彩”概念一经提出,势必造成其与“水墨写意”潜在的概念对立,从而加剧了双钩画必须细谨、水墨画必须放逸的荒唐认识。由此引申出影响颇大的另一种观点,即中国画的优长乃是“写意精神”,其实在学理上同样不能成立。写意精神亦即自由表现,是包括西方绘画在内的所有优秀艺术的共同品格,无论是提香、伦勃朗的油画,还是宋人双钩花鸟、水墨山水,无论其效果多么严谨,其实皆以放逸的笔触挥洒而成,怎能将此种表现仅仅视作中国画乃至文人画的专利?事实上,如果将旧式文人的随意化表述也即“工笔”与“写意”,作为学科分类的依据,必将造成将形容词混淆于名词的后果,换言之,如果将“工笔画”视为画科,那么“严谨的画”是否同样可以成为画科?而此思维之所以会成为定势,则不可不归因于大写意的一度风靡,挤压了其他画风的生存空间。 从艺术家行政化、官员化到艺术平民化、娱乐化 除了学术的思维定势,还要附带指出体制造成的思维定势。建国后,艺术家的行政化与官员化成为体制,这对于当年文艺服务于政治,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红色经典”的诞生,从根本上是依托于这一体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与学术风气的日渐开明,这一体制非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以往的功能,反而在艺术商品化的催化下,造就了“官本位艺术”的丑陋现象,更何况这一体制,还助长了非学术性的地域文化强势,是即前文中提到1950年代以来大陆国画界潜在的思维定势。 艺术的地域性差别自古有之,所谓“齐鲁之士,惟摹营邱;关陕之士,惟摹华原”,便是宋代地域性画风的写照。需要说明的是,齐白石  所擅长的大写意原属江南画传统,在民国时广泛影响北方,而张大千 所擅长的大写意原属江南画传统,在民国时广泛影响北方,而张大千 等追索的唐宋画传统,在二十世纪最初却是在北京由金城首倡,后渐影响南方。正常的学术交流是艺术繁荣的基础,但若遇行政干预,不免产生微妙变化。明代画史上发生过著名的吴浙争锋,当时吴派领军人物沈周 等追索的唐宋画传统,在二十世纪最初却是在北京由金城首倡,后渐影响南方。正常的学术交流是艺术繁荣的基础,但若遇行政干预,不免产生微妙变化。明代画史上发生过著名的吴浙争锋,当时吴派领军人物沈周 的弟子,在浙派势大时竟转学浙派绘画,而浙派代表画家蒋蒿之子,后来则在吴派势大时转习吴派风尚……这种现象,对艺术而言绝不美妙,优秀艺术也因之会成为“审美疲劳”。在坊间,北方人视齐白石 的弟子,在浙派势大时竟转学浙派绘画,而浙派代表画家蒋蒿之子,后来则在吴派势大时转习吴派风尚……这种现象,对艺术而言绝不美妙,优秀艺术也因之会成为“审美疲劳”。在坊间,北方人视齐白石 为“第一大画家”,港台人则视张大千 为“第一大画家”,港台人则视张大千 为“第一大画家”,类似的争议,不知能否用行政方式予以排解? 为“第一大画家”,类似的争议,不知能否用行政方式予以排解?上述的思维定势,是艺术的地域性与行政性交融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后文人画反弹、西方现代艺术潮涌的情况下,不仅对治学严谨者产生过影响,而且对如《点将录》之类的近现代画家评传,影响至深。此类著述,也几成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榜单。艺术家、学术家固然需要宽松的环境,但宽松的环境未必是优秀艺术与学术产生的必要条件。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文艺平民化与精英化的差别将日趋显著。平民化势必推动文艺的娱乐化与非主流化,而今“山寨”现象的活跃,便是例证。当代中国人正处在摆脱以往文艺唯崇严肃化的时期,然而尽管平民化乃大势所趋,但以广学博讨、功力锤炼为特征的严肃艺术毕竟仍属当代文艺的重要内容。重新感知文艺娱乐功能的当代人,不妨将美术史研究亦视作娱乐,但类似的“研究”毕竟不足以成为传之久远的“定论”。而以对“定论”的思索为起点,近现代中国画或许也具有了新的认识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