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静泉逾响
——浅谈吴秋雨诗意栖居的山水家园
文·陈裕亮
前不久,福建省一位很有修养的领导问笔者,吴秋雨的画如何?答曰:画得很好,路子很正,修养相对全面。又问曰:那名气好像不太够,为何?答曰:他在画画、写生和读书之余,忙于艺术策展,结识团结一批艺术名家,关键在于他给福建籍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展示的机会,对自己的宣传也因此耽误了!他把个人价值转换成社会价值,有着忘我的情怀,也是他对人生哲学价值观念的体现。闻罢,领导颇有深意地点了个头,说了句:他对得起福建画家这四个字。这就是笔者眼中的吴秋雨,一个出生于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福建诏安,画家、诗人、艺术策展人。
推陈渐出新
看吴秋雨的山水画,第一感觉便是路子很正,笔墨修养也不错,但是形式感很强,很让人记得住。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认真的品读之余,深深体会到画家吴秋雨注重传统,注重笔墨,但传统似乎对他完全不构成束缚,他利用前人的经典图式进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形式感极强的个人图式。
吴秋雨有很多青绿山水作品,画面中有着北派山水高大宏远的气势。像作品《南雁心象》中,有着北方山水雄伟的山形以及奇峭的笔墨,初看起来,近处的松树仿佛与大山不太搭调,它们不似北方大山的遒松劲柏,而多了几分柔情,几分妩媚,更像是出生于江南水乡。因此,总感觉它们不能与画面相容,像是硬生生加上去的。但再细细品味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貌似北派的名山大川也完全不是像北方山水画那般以深墨清晰勾勒或用硬性的皴法描绘北方石质坚凝的山体,相反,他的用笔甚草草,走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这种淡笔模糊的印象式画法营造出笔墨柔和、平淡灵动的视觉氛围和相对松弛、疏密有致的空间关系,将草木畅茂、林麓烟霏的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吴秋雨的青绿山水更接近于表现南方山水。
在构图方面,吴秋雨也十分擅长揉合南北山水的特点。一般来说,北派山水往往采用“以大观小”的鸟瞰式的视角,不拘于一个角度而将宏大的万水千山、丘丘壑壑都浓缩在画面的尺寸之间,彷佛给了观者一双千里眼,甚至可以“自山前而窥山后”。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则认为北派山水高远、深远的视角拉远了主体或观者与山水之间的距离,转而采用一种压低了,拉近了的“平远”视角,以契合文人所追求的“居栖”审美取向,从而将构图的重点转移为景物之间生动的联系和渗透,通过图面各部分之间的和谐来营造心无交融的精神空间。
在吴秋雨的作品中,能看到元代倪瓒三段式构图的影响,但他又对这典型的文人画图式进行了改造,像《齐云山》、《烟雨土楼行》等一些作品,画面中有着南方山水的平淡致远,但视角又不仅仅限于平远,而是拉远,拉高,有的作品甚至近乎鸟瞰,但是心理距离却没有被拉远,画面中却充满了亲切和熟悉感,依然可望、可游,可居……这其中的原因,大抵是他能够很好的安排横与竖的关系,使看似简淡的画面实在隐藏着严密的层次感。像《黄山》系列、《太行山》系列等作品,最远处的背景是连绵不绝的山群,接下来则是茂叶的秋林和宁静的河溪。但这些往往只是充当背景,艺术家总是能将人们视线的焦点聚集在近处安静的小亭子,温馨的土楼或者悠悠松树之上。如此,便使北方山水的形式和南方山水的意境并行不悖,同时也做到平静的美感与现代的动感并存。在这种种横竖、虚实的构图跳跃和空间层次中,做到层层展开、均衡对称、虚实相生。在借鉴了许多西方艺术的空间构造与画面张力形式的同时,又隐含着中国的虚静简逸的终极精神追求。
山静泉逾响
中国传统文人画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中有诗”是对画家要求很高的一种境界,并非以画中有无题诗来衡量,画无诗意,即使题上诗词,也索然无趣。与今天大多数艺术家不同,吴秋雨有着较深的文学造诣,他的画,偶尔自撰诗词题于画面,诗情画意,相得益彰。也有很多只在边角处签名钤印,但仍然给人感觉诗情洋溢,意境清新有书卷气。而且不论他画的是什么题材,这种诗情画意始终在他的笔下蔓延。究其原因,非科班出身的他有着求知的欲望,执着于传统国学。而立期间负极北上,在中央美院进修期间,曾问学于当代诗词大家周笃文先生,经周先生的传教,得益匪浅,对传统诗词也颇有见解,与古代文人画家有几分相似之处。从事绘画对他来说不是“为人”的社会压力,而是一种“为己”的自觉自愿,而且他做到了苏东坡所主张的“诗画同一律,天工与清新”。其中的“天工”是指真实、自然;而“清新”则是新鲜活泼,别具一格,使他成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艺人。
诗意是吴秋雨山水画的共通之处,也是其灵魂所在。笔者与秋雨兄交往不少,却不曾问到其对王维先生的山水田园诗的感觉,只是更多的是听他对于堪舆和命理的理解。说句调侃的话,他似乎更像个研究易经和相术的术士,与山水画似乎不沾边。但是观其画甚多,笔者总是从中感悟到王维先生“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山水神韵,感悟到“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那种活生生的感觉,还有那“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种情景融合的雅意。一言以蔽之,吴秋雨的山水画处处传达出王维先生所说的“山静泉逾响”的意境。
诗意栖居的家园
这诗情画意在今天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世界,有着更多的现实意义。
法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应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又赋予“诗意栖居”哲学的意义——人生在世不应该只是为了劳作而备受折磨,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沉迷娱乐消遣而不能自拔。而是应该以神性的光芒映射精神的永恒,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
在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中,诗意栖居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求。城市变得霓虹闪烁,光鲜照人,人们却愈发感到繁华散尽后的冷清和寂寞。觥筹交错,呼朋引伴,却也掩盖不了内心对城市的陌生与疲惫感。
在吴秋雨的作品中,海德格尔对于人类理想生活的抽象期盼,变得具体而生动。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钢铁世界的另一面向,充满无限的生机与想象。跟着他,走进古拙朴质的八闽乡村,徜徉于弯弯曲曲的林间小路,路过参差不齐的福建土楼,沐浴着扑面而来的缠绵小雨……记忆中最美的家园,魂牵梦萦的故乡,那样的安静、唯美,所有的情绪都在观赏作品时释放出来,一瞬间,我们仿佛暂时远离了世俗的纷繁和人性的嘈杂,内心是那么的平静,静的似乎可以听得到房檐上水滴落下的音和叶片上一只小虫的鸣叫。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天地造化的“大美无言”和充满温情的生机勃勃,哪怕只有片刻,也足以温暖人心……
正是这种蕴藉隽永的诗意情怀,使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景物,在画家的笔下得以升华和诗化,使画家的山水画作品超凡脱俗而又余韵无穷……
艺术学基本原理认为,自然界的景物和生灵,都对人类自身的生命都有一种激发和唤起的作用,能够陶冶、滋养人的情感意志和思想品格,成为人们精神生命的养料。吴秋雨作品中那些生机盎然的山林、密密麻麻的土楼,在这里都成了一种文化的符号,向观者传达着一种文化的意味和指归。让我们在回眸生活的瞬间感悟诗意和美好,让“诗意栖居”在纷繁的世界中有了现实的可能。
(陈裕亮现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工程“中国画发展风格取向及其案例研究”课题组秘书长兼首席专家,兼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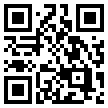
吴秋雨 微官网
请保存,可以印刷到名片或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