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传统,继往开来”观齐志强诗画有感
齐志强画集作序
中国画是大文化的产物,是包含着哲学、文学、书法、历史以及画家人品、修养等因素综合载体,是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视觉化文化样式之一的表现艺术,历代文人在不断探索宇宙自然奥妙的同时,逐渐不满足于描摹客观物象的外在描绘,一直具有强烈的精神性和自我中心的态度。有了历代文人士大夫的介入,绘画就成为中国哲学内涵的创造,而笔墨的创造与发展更加强调了语言体系的逐步完善,笔墨和形式应用在创作实践中,升华到追求精神探索的至高境界,文人画由此而诞生。自文人画兴起以来,画家极为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
北宋苏东坡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载体。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文人画占有比较高的地位。以诗入画,是古代文人仕大夫一种闲情逸致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注重本身学识涵养以及个人的品德。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所谓文人画,仅有笔墨功夫是不够的,作者还得把自身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与笔墨交融,达到了诗画相融的最高境界。
儒、道、禅三家文化对中国文人画的影响颇大,历代文人画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家哲学思想体系,儒家主修身以道,治国齐家平天下,为政在人;道家主忘,道法自然,物我两忘,主静;禅家主空,得意忘形,四大皆空,主灭;这三者的思想殊途同归,让画家从本质上得到了心灵的启迪,也从境界上达到了转识成智,意境超然。
元代文人画,“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 四家为代表,他们更注重以意为象,用笔简练、意境幽深、神形兼备。
明代文人画的代表董其昌,他饱览群书,以儒家学说为本,以“程朱理学”及“禅宗”一脉为源,把“禅宗”那不羁物欲而求大自在的精神文化内涵贯注于书画作品及诗文之中,从某种角度解读了绘画的表现语言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这从他独出机杼的诗、书、画论文中可窥一斑。尤其是他以“禅宗”的“南顿”、“北渐”比拟“积学”与“会心”的艺术观——南、北宗论,更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化修养。他善于追思,以自然之理诠释宇宙万物,以文人的笔情墨韵体现超然物外的清静之境。他把文人画中笔墨超逸、意趣神妙的一脉定为“南宗”,把文人画中状物凝形、法度森严的一脉定为“北宗”。这一理论,是他在多种文化修养的基础上产生的联通学问,是自然与心境交融后的自我思想的大自在、大自由的抒发。
清朝以“四王”为代表的“笔墨核心”论,为创造状态的主流派绘画逐渐统领中国画坛,造成了图式表现的程序化现象,形成了手法上的单一和视觉上相对雷同的定式,在笔墨语系的创建上并没有多大的突破。其作品虽飘逸空灵,但过于轻佻;虽笔简境幽,但空洞乏味,缺乏个性、缺乏思想。而体制外的四僧,倡导:“以古人为友,以自然为师,”对人生有了与众不同的乐观,豁达与自我反省,超越笔墨的程式化,到自然中寻找新的符号,直达艺术精神的底蕴。石涛提倡:“无法立法”,“笔墨当随时代”的口号。让清朝山水画有了超越性的发展,证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体系,印证了中国哲学、美学思想的真谛。
近现代山水画四大师:张大千、黄宾虹、陆俨少、李可染他们都是继承传统文脉而逐渐蜕变出来的。
上述所有具有创造和开拓精神的中国画大师们都给了我们无穷的启迪。他们对我法与他法、今法与古法的辩证关系,都能持有冷静而科学的态度。在弘扬民族文化的道路上,“各有灵苗各自探”。不论以哪种方式,他们的治学方法,值得试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画家们借鉴。
志强兄是个执着于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是个善于借鉴前人治学方法和执着于传统文化的艺术家,他脚踏实地,秉性坚贞,不以世俗厉害于胸中,不以时代好尚感惑其心志。他从小就临摹大量的古画,对宋元明清笔墨技法有着继承和转换。他喜欢读书、喜欢传统诗词,多首诗词曾在专业报刊发表并结集成册。他能闹中取静,能沉潜深入文脉核心。从画面可以看到志强兄扎实的笔墨功夫,他的扇面小品“舍南舍北皆春水”,用传统小青绿画法,岩石皴法笔墨厚重结实,远山彩墨淋漓,桃林环抱村舍,拱桥后泉水潺潺,前面粼粼湖水荡漾着几只小船,飞翔的群鸟给画面增加几分生气,这分明是江南小景。画面构图完整,远近分明,飞鸟、船只、小桥、流水、人家,诗情画意,引人入胜,是个理想的桃花源,是生机勃勃的春天故事,是文人墨客最向往的地方。
扇面小品“皖南秋韵图”,白墙黑瓦,高耸梯式的马头墙,明显是徽派建筑,右边的瀑布和村前小径开合呼应;红色的树林是秋天的信息,层层白云排列有序,把山的层次推远,画面透亮鲜明、秋高气爽,让人赏心悦目,有着宋元笔法遗韵,意境高古。
还有横幅画卷“太行瑞雪图”、“有余图”、“高士幽居图”等都是用宋元古法来描写当代生活情景,古为今用、他的艺术风格是用前人笔法来师造化,他对中国文人画有着逐步深入探讨,所谓继承传统本身就意味着创造与变化,没有创造的继承是固守陈规。任何事物都须在创造中才能得到发展,这是他对学问的一种态度和个性成长的过程。吸收前人精髓,得其理趣,胸怀洒脱,从静默的沉思,转换为心灵的创构,化实景为虚境,用传统的笔墨,创作理想的自由家园,是他自我精神世界的展示,是其丰富的学识修养和独特的思想观念等因素的综合体现。
绘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正本清源”是当代梳理传统文脉的口号,是继承与发展的唯一途径,是时代精神的整体结晶。董其昌曾有这样一句名言:“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这句话强调了“师前人”与“师造化”的先后顺序。当前有些人耐不住寂寞,胸无点墨,对传统不理解,反对复古,大谈创新,重复性地制造垃圾,作品低俗无味,不堪入目,投机取巧,不择手段地行骗江湖,污染社会,误导国民。
一部分新潮美术家“反传统”观点而具有民族文化维权的倾向,画家试图在追寻传统文人画脉络的基础上展示当代文人思考的语境,而由于其文化基本功的不足和价值取向的有别并没有突破传统文人画的羁绊,在笔墨的追求上虽力尽“精妙”但并无大的突破和创造,之所以被学术界关注并引发讨论,这也是对当下“反叛”和 “媚洋”倾向的批判。同时也可以平衡人们在躁动中回归雅静和谐的心理追求,应该承认这一现象对重新开启中国画返朴本土文化和语言回归笔墨意识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画及笔墨语言发展思考的相对冷静与成熟,他们的作用和价值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在这个浮躁和现实的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文化意识,已被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意识所替代,大家都在追逐金钱效益,讨好买家,养家糊口,攀比外在的生活方式,内在贵族性的精神生活,在人们功利的目光中,已逐渐瓦解。作品习惯以金钱来衡量艺术价值,审美标准一片苍白。真正能够守望着传统文人画的艺术家就显得难能可贵。
清人方亨咸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绘画,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
由此可见,一个画家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不断的磨练和研讨、消化,才能够慢慢蜕变,逐渐形成自己的面貌,所谓:“厚积薄发”。
每个画家都有阶段性的成长过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志强兄可谓真知灼见,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勤于耕耘,他能够把所有的感情尽情挥洒于山水之间,寄情造意,诗从胸发,画由意出,诗与画在意境上的交融,赋予了真正的气韵生动的美感,也逐渐形成他高古的绘画形式。今其面貌只是代表这阶段之水平。不惑期间,艺路甚远,他还会去自然中寻找自己的笔墨符号,以他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笔墨功夫,来丰富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他的艺术个性,通过传统文化和生活阅历的洗礼,上下求索,逐渐完善自我的笔墨形式和脱俗的艺术境界,促进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不断的探索和提炼,我相信他山水画能够获得新的生命。
癸巳年夏月于北京宋庄思逸草堂 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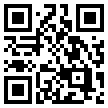
吴秋雨 微官网
请保存,可以印刷到名片或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