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水画的形式与意象
形式作为绘画独立的精神载体,是以点、线、面、色彩、节奏、肌理、结构等构成因素为知觉感知的绘画存在方式。形式建立在生命的精神参与与投射当中,是生命寻找、满足自身完整与内心渴望的一种精神活动的反射方式。意象是艺术活动得以精神满足的基础,这种精神活动的满足与实现是在绘画形式生成意象之后完成的,所以雷体沛说:“感性只是艺术作品的一种手段,而意象才是它的真正目的”。所谓意象,就是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即以夸张、变形、重组或突出结构特点等手法,以对客观物象的感受为主旨,强调心理真实的精神意蕴。绘画作品正是形式与意象的统一体,这种统一就是把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对自然形态的认知和情感历程的依托,通过绘画的视觉形式要素构成新的序列关系,从而表达出画家独特的审美意象和精神世界。
八大山人(1626年~1705 年)原名朱耷,江西南昌人,明朝宁献王朱权九世孙。明灭亡后,落发为僧,法名传綮,字刃庵,是清初画坛“四僧”之一,曾用雪个、个山、人屋、个山驴、驴屋、道朗等号,晚年(1684 年~ 1705 年)号八大山人。八大山人曾饱受丧国之痛,阅尽人间凄苦,其思想融儒、道、禅等诸家于一体,他将自己的全部情思都寄托于风格鲜明的书画之中。
八大山人一直以构图疏简、造型孤怪、沉郁凄楚、意境苍凉的画风而名世,其花鸟画早在其中年时期即已蜚声画坛,而山水画却因起步较晚,且为花鸟画盛名所掩,未能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然而凭着多年的花鸟画笔墨修养,其山水画亦直入巅峰之境,在绘画形式构成上甚至胜过花鸟画,有着其花鸟画不能替代的独特的美学价值。山水画以深沉的政治寓意和隐逸情结契合了八大山人的心灵,这也正是其晚年落笔山水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山水画进入成熟期后,画幅增多,仿迹渐少,形象凝炼,表现形式更加纯化,画中的山、石、土坡、峰峦等造型简约,笔势沉着痛快,用笔自然圆浑,不再出现早期山水画中那些圭角和生硬的边线。画中远山多以圆角的三角形式出现,近处山体造型多出现三角形、四边形、梯形等结构性的几何形状,这种几何形态的动势显得轻松自如。实践证明,这种结构性的表现形式,更具有恒久的稳定性,蕴含着节奏和韵律的美感及超越客观物象的精神力量,有着持久的审美表现力和艺术生命力。
在八大山人的山水画中,山体或山石阳面多留空白,阴面山体在结构性的块面基础上以铺染为主,而不强调皴笔和线条的运用。铺染使画面达到一种自然率真的意趣,呈现朴实苍茫的视觉效果。这种平面性的铺染表现是对传统山水画皴法的弱化,而强化了铺笔的渲染功能,形成山体的整一化效果。八大山人一反前人因运用过多笔墨表现山石向背而削减了山体的整体性表现而造成画面繁冗失序、节奏混沌的弊病,突显了山体的整体性结构美,这也自然为前景的树木植被作了更好的整体性铺垫与衬托。这种强调沧桑韵味的表现形式无疑契合了八大山人遭遇家国倾覆之痛的深沉基调,也符合其寄情于“残山剩水”的凄楚之情。
八大山水画中前景、中景、远景物象叠合,这就混淆了人的视觉直观感受,强化了错觉的作用。叠合的平面性结构感为画面增添了新的视觉景象,这种形式造成树木、山体浑然一体的空间视觉效果。正像格式塔心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考夫卡(Kurt Koffka)所说:“艺术品是作为一种结构感染人们的。这意味着它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的集合,而是各部分互相依存的统一整体。”这种构成形式使八大山人的山水画摆脱了应物象形和常规构建山水画面空间秩序以及物象形体比例的缚,达到一种新的构成性表现境界。这是对正统山水画组合有序的空间构成方式的削弱,它一反传统山水画景物间的构成层次与秩序,弱化表现物象的形体边界,强调整体画面的融合性。
树木是构成山水画的重要物象,是山水生命气象的表征之一,其荣枯华实关系着山水的生气活力与精神气象。在八大山人的山水画中,树木是宣泄情感最为重要的形式。如果说平面性铺染的山石、峰峦是八大山人生命交响曲的基调,那么前景的树木就是他生命之曲的主要旋律。其所画树木不仅形式简约真率,而且造型怪异夸张。首先,八大山人突出了树干在视觉中的体量作用,强调了树干形体的张力,减少枝叶与树干的比重,树干少皴甚至无皴,树干形态或孤直或扭曲,倔强刚强,如蛟龙升空。这种形式张力使八大山人摆脱了绘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而突出了精神性。
其次,一去传统山水画中树木枝繁叶茂的景象,出枝较少,但不乏变化,姿态寓静于动,树木参差呼应,似人欲言,给人以枯淡、孤怪、寂寥的视觉感受。再次,树叶疏朗淡然,墨色清韵,错落有致,甚至只寥寥几笔于树冠之上,既指意明确,又言简意赅。这种极其浓烈的形式意味契合了八大山人心中的孤寂与荒凉,正如范曾所言:“八大山人的画,简约至于极致,那是真正的妙语不在多言,真正的至人无为,大圣不作。……简捷清醇,精微广大,高明中庸,扫尽一切的繁文缛节、一切的矫揉造作、一切的事功媚俗。”其实八大山人早期的山水画就已呈现出用笔精简、意境萧索的倾向,这在其56 岁所作《绳金塔远眺图》轴和故宫博物院藏其早期署名“驴”的《山水》画中,即可找到明证。这种单调简散的组合形式表现出清幽淡远、空寂、荒寞的视觉效应,俨然成为遗民隐士心中向往的那份净土,也是对中国画以意造型最典型的诠释。点语言是八大山人绘画情感的调节剂。
“点”在中国山水画中起着重要的形式构成和装饰作用,不仅丰富了绘画的形式语言,还承载着情感的表现。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点苔》有言:“画不点苔,山无生气。昔人谓苔痕为美人簪花,信不可阙者。盖近处石上之苔,细生丛木,或杂草丛生,至于高处大山上之苔,则松耶柏耶,未可知。”点不仅调节墨色和线条的对比,而且对于分割空间也起到有效作用。这种最具表现力、抽象性和形式意味的“点”在八大山人的山水画中成了情感强有力的调节剂,其山水画中的点较之其他画家更具表现性。在八大山人的作品中,点主要用于铺染山体阴面处,其形态丰富,以横点为主,大小相应,书写性强烈,抒情之感跃然纸上,且墨点浓重,情感饱满浓烈。在浅淡的远山背脊上,点以竖点形式三两错落攒聚,仍用浓重墨色,愈显生动别致。八大山人山水画中点的分布与山体、树木形成有趣的呼应,富有抽象的形式意味。点调节着画面的节奏与层次,最为重要的是,它通过分布和呼应,承载了八大山人更多的情感,而不仅仅作为装饰性和象征性事物。
20 世纪初至50年代,对绘画形式的深入探索成为西方美学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早在1913 年,英国美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就提出了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强调了形式的第一重要性。虽然其在逻辑论证上有失严谨甚至矛盾,但仍然不失为有价值的见解。他说:“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
合,这些审美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尔深刻地触及现代美术的情感“意象”和“形式”之间的微妙关系。
绘画实践表明形式具有双重品格:一方面它是形式,这是相对于意象而言;另一方面它又是内容,则是相对于表现而言。形式即是绘画个性化语言的外在显现,又是藉以表达内在精神意象的载体,“由独特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审美内容,是任何规模、任何样式和种类的艺术所不能缺少的。它是艺术特有的个性,是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标志”。在这种具有个性的形式背后,是八大山人独有的心象,而独创性的本质即在于绘画形式语言的个性表达。这正是现代艺术价值体现的主要特征之一。马蒂斯说过:“首先,神圣的艺术需要良好的道德卫生。我唯一的信仰就是热爱创造性的作品,热爱创造和巨大的真诚。”所以无论表现内容积累得多么丰厚,如果没有理想的表现形式,同样无法达到情感表达的目的。八大山人在形式—形象—意象的链接中找到了情感的物化形式,并产生共鸣。
明清以来,中国画形式与意蕴间的转化趋于定型,完整的创作体系依附于完美的程式规范,定型和重复使中国画丧失新的形式语言和意蕴,失去纳新的能力,从而失去形式意蕴与心理感受的真实。而为什么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却有一种特别令人感动的力量,清冷凄惨之意直扑人面呢?独特的绘画形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形式最为直接地嫁接了八大山人作品的精神意象。这也正说明了八大山人找到了宣泄情感的最佳形式载体。这与西方由外在形式挖掘内心世界的现代绘画即“知觉自然”到“探知内心”是一致的。吴冠中先生早在《关于抽象美》(原载《美术》1980年第10 期)一文中就曾提出:“八大山人是我国传统画家中进入抽象美领域最深远的探索者。”抽象不是停留在点线面的形式主义游戏之中,形式只有与意象共鸣才有灵魂,只有通过共鸣,形式才得以生存,并且由里向外产生作用。这种形式使表现语义更加纯洁,而脱离了物质本体,使绘画不再是一种与被表现事物本体的对话,而是人对自我内心的观照,即“缘物寄情”,成为作者内在精神世界的的反映。八大山人正是通过形式所具有的意象性功能表达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对点、线、面、肌理等形式语言元素的组合、排列和强化,不是对自然简化描述,而是综其学养、阅历和人格气质等进行自我观照,否则,形式将空洞虚浮而失去生命。
八大山人以崭新的绘画风貌、独特的表现形式,拓展了传统绘画语言,其山水画艺术更接近抽象艺术的范式,也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和未来方向,孕育了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精神。八大山人作品所表现出的焦虑、失落、凄楚、空寂和苍凉,正是形式语言发挥作用的结果,正如艾中信所言:“凡属真正的艺术品,尽管它画得如何具体,以致于达到逼真,那抽象的形式因素,到底还是比生活本身活跃而生动。”虽然它无意于再现自然本体,却有作为承载人类精神的介质的可能。
在一体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冲突与融合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驱动、情绪的浮躁、艺术品的商品化等因素使中国画的负面问题越来越严重。八大山人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如何尊重绘画,彰显绘画精神。绘画创作应将时代精神灌注于对传统的理解与发扬。当代中国画艺术应更加关注生活,感受生活,彰显生命精神的宏大,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激活传统文化精神,而不是追逐名利,或追求已经僵化的形式和“漂亮”的笔墨外衣。现代绘画艺术需要面向未来作创造性探索,寻找承载现代人精神和情感的形式载体,自主地营造新的绘画构形规则和范式。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未来文化,放松绘画概念的界定、材质的限定以及笔墨至上等思想,立足传统精神,并融汇中西,才是艺术家们努力的方向,也是八大山人作品带给我们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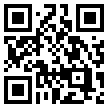
康君 微官网
请保存,可以印刷到名片或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