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我•绘画
自然,是圣人“含道应物”生发寓理的基源,也是画家“澄怀味象”感通艺术精神的凭借和载体,中国画早从魏晋时期涉足山水,就说明了人类在满足自身、寻求自由精神方面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画家通过自然之象与“道”相通,借自然之象通达人性之自由境界,让自然引领心境,离形去智,体察自然的博大和深邃,绘画之境也将随着对自然的体悟而深广。
自然,蕴含一切法则和审美意韵,在人的眼中是一个无限的世界。绘画和自然有着同一的无限趋向性,这种无限让生命从现有实在界的困顿和囿限中得以解脱,在人与自然触动心息、物我两忘的瞬间,“我”早已分解于自然的形色之中。感性自然,建立意象的无限世界,这正是画者精神超越,通达自由的渴望,意象的无限性正是艺术永恒存在和生命寻求的根本,自然是激发画家创造的感性之源;没有感性触发,绘画也将失去情愫和生命;感性是画家与自然交汇的投射口,虽然感性还是实在界的有限结合。但缺失感性的笔墨必为泛泛之式。“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绘画的一切法则本源于自然,万象有形,形生差异,却尽归于“道”。看似静态的自然,却给了我们无限智慧和潜在力量。
中国画的笔墨特质在于与情感、审美价值的契合,这与西方传统绘画语言表述有着根本的不同,笔墨是中国文化的情态特征,笔墨润涵着中国绘画精神层面的重要内容,笔墨的重要不言而喻,但笔墨的意义是以个性化精神的传递为基础,不要让笔墨成为取宠的砝码和迎娶他人青睐的嫁衣,笔墨应由内在的感受而生发于外,这外在的笔墨才有灵魂和存在的意义。笔墨观念的开放是绘画变革的前提,如此笔墨的传达和表现才有更多的可能性,不然笔墨语言的发展到宋元代时代也就可以了结了。也不会出现黄宾虹、林风眠、这样开拓性的大家。其实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笔墨变革的诉求,当然谈笔墨只是局限于绘画语言的层面,笔墨的背后是绘画观念的反映。绘画离不开技能,创新不是简单地技法改变,它是与绘画理念,笔墨语言、造型达意、形式构造,立意造境相匹配,创新是全方位的变革。如今笔墨成了中国画变革的瓶颈,那是因为画者还缺少综合统筹的能力,单一和自闭必然导致恶性循环,依附更多的是笔墨带来的自足,视乎把笔墨看做通达中国画艺术的唯一救命稻草,因为除了在乎笔墨,其他已是无能为力。
绘画上赋予笔墨的承载力越多,约制其外展发挥的可能性就会越少,笔墨本身依附于形体就是一种负担,这与书法的纯粹线性不同,如果绘画中的线条照付先前的程式与经验去承接新的形态和语境,必然又促使其走向回归先验复制传统的境地。艺术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是适应时代生态进化的过程。绘画创作就是将时代精神灌注于对传统的分解与铸建之中,创作是包容后的纯化整合过程,创新是建立在传统范畴基础之上并赋予新的意义,就是绘画传统精神和创新关系有效内化,以及自我感受和表现的外化实践过程。变革是历史的必然,是画家内需的驱动力,是在分享一种观看方式。
继承和创新永远是一个古老而鲜活的话题,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在艺术发展中,继承是手段,创新是目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传承的存在方式是致用的选择和结果。传承即有物质属性,又蕴含精神介质,只有激活传统的精神介质,才可言其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借古开今以不断适应新时代人们对于审美的需求。时至今日,绘画传统精神仍然受到遏制和曲解。传承精神不是传承表面程式,只有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和发展。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始终处于一种动态之中。不同时代对于传统的解读都有以时间为条件下的不同诠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视角和价值取向。在美术史长河中不同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认同各自泛着奇光异彩。那传统到底是什么?是唐宋形神兼具的人物画;宋元法度完备的山水画;还是明清借物言志的花鸟画,面对丰厚的历史积淀,每个画家都有各自的判断和取向。
“遵循传统者”是在他熟悉的世界中辨认出熟悉的代码,去证实我们已经找到的东西。而对于”革新主义者“来说,希望为新实践找到证实的愿望,去修改以往的代码。艺术家的作品不知不觉地提供了一个强化性的符号,这个符号能为我们眼中的自然视像进行编码,这也是中国画程式化形成的重要依据。但这种强化和提炼应是感受后的升华,而不是无视感受的断然模仿。绘画犹如一个自设的“陷阱”或“圈套”,
又像一场“闯关游戏”,规则备注难度,观念决定着她的形态和水准。是落笔于程式,不断复制模仿先验,还是置身荒漠,勇于挑战,赴会未知的境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因循”还是”抗争”是一个不小的考量。美术史一直在传承下变革,但任何时代的变革也没有像近现代时段上发生的如此仓促,“山乡巨变”数千年的农耕社会急转而向工业文明,我们甚至来不及太多思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革时代到“85”新潮等革新思想中,中国在各种艺术流派的现代性试验中艰难寻求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探索我们却还知之甚少,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与实践积累后的的时间检验,虽然有时理论新鲜却不乏空洞,成了一种表层概念,模拟之多,创造之少,这必然流于平庸,更与伟大作品无缘。伟大的作品就在于她充满神秘和模糊,其中掺杂着焦灼不安的情绪与矛盾,甚至躁动和疑惑。以西润中,中西调和是中国画变革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美术史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绘画倾向和潮流,中西调和是代表着现代中国绘画的时代精神,多元化融合是中国画未来的发展方向,气韵、线性、感受、调和这四项应是构筑现代中国绘画内涵和生命的基本特征。
以自然的生机触动笔墨,以内化心源提升境界,以西润中调和形式,中国画的变革仍然有着更多的可能性。中国水墨必将生生不息,水墨未来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绘画体现的是一种智慧,一种信仰,一种修炼。当专注和沉默绑定绘画;当自己成了一种虚拟存在;在一切没有转换回归现实之前;绘画才是绘画。
走进自然,我与绘画永远在路上……
康君于罗通草
2016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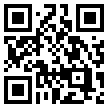
康君 微官网
请保存,可以印刷到名片或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