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美人——漫谈古典艺术中的美女形象
美人,这个经久不衰的题材,在历代文人的笔下被赋予了丰富的艺术生命。但这种被赋予的内涵,多数时候是把女人放在客体的位置上,以同情、欣赏或借喻的方式给予关注。虽然也有个别女人受到男性社会的垂爱,但仍摆脱不了男人居高临下的俯瞰,在这样的视角下,女人自身的感受和价值轻如鸿毛,话语权的缺失使整个社会乃至历史都习惯了按照男权思维来看待女人。&
#60;?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从春秋到两汉,从诗经到乐府,东门赴约的踟躇少女,被“抱布贸丝”的男人始乱终弃的哀哀弃妇,鄙视贵胄调戏的采桑女子,艰辛劳作的山野村妇,无不反映了现实中的女人的弱势,以及她们的无奈、哀婉和坚忍。这些以女性口吻娓娓诉说的诗句,因源于民间歌谣而显得质朴生动,也因其作者的平民身份而凸显了庶民阶层的真切情感,那种打动人心的简洁率真,在隋唐以后的士大夫作品中再也难觅踪迹。
不甘美人为残酷的现实世界所亵渎,使人们生发了种种意迁神女的想象。弄玉吹箫引凤,是酷爱音乐的公主脱胎换骨的佳话,魂断马嵬坡的杨贵妃,在诗人的笔下归隐仙山琼宫。在《神女赋》和《高唐赋》中,讲述了两代楚王与巫山神女暧昧云雨的传奇经历。而唐代的诗人则假借神女的名义,将流莺之所描写得荡人心魄。魏晋神手顾恺之,以自己的生花妙笔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美女典范:眉如翠羽,领若虮蝤,明眸皓齿,腰如束丝。清瞿的面容略带忧伤,曳地长裾飘然若举,这和同时代的佛教造像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北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也是这样消瘦而轻灵,仿佛在乱世中无处栖身的凄凄芳草,自有一种脱俗出尘的仙风道骨。同样出自顾恺之手笔的《女史箴图》,改换装束的贤妻良母不再被神性光环所笼罩,克勤克俭的谦卑恭谨还原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真实形象,象一面历史的铜镜在幽暗的绢面上反射着旧世界的光芒。
唐代的开明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表现在妇女的服饰中,不但有裸胸露背的各色长裙,还可以穿裤装衣胡服,对着衣的场合和底线也没有太苛刻的要求。女人们抛头露面的机会更多,没有北宋卫道夫的指指点点,没有元代蒙古蛮夷的民族歧视,没有明清折断趾骨的裹脚布,生活在这个时代,比起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期的女人要幸福得多。即使如此,大多数女人仍然摆脱不了悲剧性的人生宿命,这在唐诗中有着深刻的反映:独守空闺的少妇,在战祸中流离失寓的佳人,孤老终生的宫女,不得善终的青楼女子;《丽人行》里,贵族妇女的华丽奢靡,被残酷的宫廷斗争碾碎,《琵琶行》中,冠世名花也拦不住“重利轻别离”的商人的匆匆脚步。和诗人同样敏锐的,还有宫廷画家。周昉、张萱的宫廷仕女,传神的再现了唐代后宫女子的仪容:樱口蛾眉,面如满月,圆肩阔袖,雍容典雅。丰满而高贵是盛唐时期强大国力炫耀下所催生的审美的必然。
在阶层森严的等级社会,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庸,为报忠心而坠楼的绿珠,不过是石崇买来的一个小妾;王献之的桃枝,再多风流往事也掩不住卑微身世背后的凄凉;纵使李渔那样懂得怜香惜玉的才子,也挡不住出嫁的婢女被凌虐致死,世上多少娇美的女子,莫不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若没有文人为之凭吊,何来“香如故”?
其实美人的标准在诗人的心目中从未改变过,那些随时尚而变换的华服盛饰、环肥燕瘦都会风流云散,惟有理想主义的芳草美人栖居在艺术的圣殿不曾离去。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曾在《离骚》中自比佳人,那句无限凄婉的“众人妒我之娥眉兮”,将一个高洁自爱,不肯苟且合污的灵魂在受到毁谤后的悲愤描写得坚贞冷艳。建安才子曹植在《美女篇》中,通过对“美女”的细腻刻画,委婉的寄寓了自己虽有美貌般的才华与抱负,却苦无良缘栖身,只能空恨红颜老去的悲叹。诗圣杜甫,在对空谷幽兰般的绝代佳人的写照中,也以同情的笔调发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的感慨,没有明珠暗投的切肤之痛,岂能写出这样深沉凝练的诗句?
坚贞,善良,端庄,娴雅,是中国传统所推重的女性美的标准。无论是帝王贵族遴选后妃,还是士大夫择偶婚配,无论是诗歌吟咏,还是丹青所指,无不以宁静安详的内美为旨,真正的绝代佳人,不是惊鸿一瞥,也非艳若桃李,而是传承着中华民族修养内涵的古典美,而真正的绝代佳人,也不是一个具体的声容行色,而是一种境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欣赏和仰慕她的芳姿,都不会以世俗的爱妒之心将她拒之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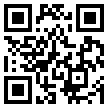
赵曼 微官网
请保存,可以印刷到名片或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