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远足与回归
编者按:曹俊是一位寓居新西兰的中国画家。所画能工能写,题材多样,更钟情于荷花。中国画家的题材选择各有其因,均与心性与喜好有关,曹俊选择荷花是因为荷花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就是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品格,曹俊更多的是以荷花作为自己处身立世的榜样,这正是中国花鸟画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曹俊的画在文化立命的基础上,融合古今;他着力于现代性的表现,使笔下的荷花呈现出异样的神采——斑斓的清,意象的韵;风动的神,雨打的意。曹俊笔下的工笔动物有自己独到的认识,这些认识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理性。他把自己的艺术创作设置在传统和现代的连接点上,置放在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上,显示了他成为一位个性艺术家的创造力。曹俊回归自然,讴歌生命,张扬个性的花鸟画创作提示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风格,也预示着当代花鸟画的一种推进方向。10月28日曹俊先生坐客晨报画院,本报记者、晨报画院执行院长田根承随机对曹先生做了来访。
田根承(以下简称田):大家都知道你2002年移居新西兰,但作为中国艺术家,你选择新西兰这个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国家作为生活、创作的空间是出于什么初衷?另外中国艺术的土壤在中国这是个常理,你有没有失去土壤的感觉?
曹俊(以下简称曹):首先感谢大家的关心!你讲得对,新西兰是个属于西方文明的国度,但她又是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国度,同时,她也有别于以工业文明著称的其它西方国家。众所周知,新西兰是以农牧业发达而闻名于世的,这与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似有几分相似,况且这里四秀如春,风光宜人,人们在舒适恬淡的环境中悠然地生活,恰如中国古代士大夫所期幻的田园意境;这里安静、温暖,无气候温差之大起大落,应该说是个读书、创作的好去处。
出国前,国内诸多师友同行也有过类似的疑惑,有人干脆直言,新西兰不会适合你的。现在满眼看去全是陌生的东西,人们所关心的事物也大有不同于国内,不用说专业的,即便是业余的中国文化团体也很难得,准确地说,找几个能坐下来清谈中国艺术的人都难,可见失去土壤的感觉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对我未必很难适应,因为在国内我就是生活在两个极端的精神世界里:一方面是古代的,一方面是未来的,惟独对当今事是看起来涉之不深,画论也好、诗文也罢,甚至于哲学,我手不释卷的多是明清以前的,我总试图在已成定论的先贤名作里找规律,以确定自己的艺术目标。诚然,“艺术离不开生活”,但是我总认为艺术毕竟是“形而上”的东西,它应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总是着手于眼下是难有大成的。黄宾虹老人就曾说过“我的画是画给50年后的人看的”,实践证明他说对了。
田:有人提出画中国画不需要写生、素材的收集有照相机就够了。关于写生你是怎么看的?
曹:写生是我们搜集绘画素材的重要手段,它是造型的基础,也是中国画骨法用笔的依据。没有写生就没有画家对自然的真切体验,绘画就只能停留在前人的窠臼里。写生能让画家不停地接受来自大自然的刺激,捕捉到生活中鲜活的真实,从而帮助画家建立描绘的自信、获得增加笔墨空间的自由。绘画的过程实际是一个对时空重建和对实体本身洞察的过程,它需要画家把从自然中找到的美和力量注入绘画里才能实现其宗教般的意义。画家在写生过程中应多拿出时间来观察,而且观察的方法也应个性化。没有个性化的观察就没有个性化的发现,也就必然没有个性化的表达。
中国画是水墨的艺术,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便有可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某种笔墨假设,而这种临场的预见绝不等同于画家在画室内的臆造。李可染先生就是非常重视写生的,通过写生他获得了表现逆光效果的个性化手法。要临习出这种效果应该说不难,难在理解他的发现,如果一味学他的画法,恐怕只能多复制品而已。为了读懂李先生初衷,我曾历时两年沿可染先生写生路线朝圣、探源。在名山川与可染先生墨迹的反复对比中,我终有所心得,并把它用于自己的创作,于山水如此、于花鸟也作了大胆的尝试。这使得我在工笔画的配景中毅然去掉了繁冗的细节,将山石的皴法全然弱化在积墨的效果中,山石最终呈现出深沉、厚重的黑色,那些前景的树木在留白的状态下似摇曳于金风之中。面对自然的写生,其目的是为创作准备素材,而不是为了彰显笔墨。写生应是对自然物象的解读与梳理,而不是急于求成的表现。表现应是画室里的事情,应把写生看作从自然中获取营养的过程。写生的收获不是看带回家多少写生稿,而是看画家理清了物象多少关系。画家每次面对自然的物象都应视自己为学童,不能带有偏见,甚至陈见。只有这样,画家才能保持好奇心,也只有这样,画家才能避免原地打转,获得提高。
观察与写生的关系有如读书与记笔记的关系。观察就是读,把要表现的自然物象当书来读,一章一节、逐字逐句地精读,并圈点出令自己感动的内容。记,不仅是记取读的结果,事实上又是一个再发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画家才能真正完成对自然物象的取舍。写生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取舍,取舍体现了画家的境界与智慧,面面俱到既不可能也不符合艺术的要旨。取舍源于提炼与灵感,所谓“纵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是也。
田:谈到中国画自然会涉及“笔墨”,有人提出画中国“笔墨为上”特别强调“笔墨”,有人则对此不屑。你是怎么看的?
曹:说到中国画,人们脑子里马上会出现“笔墨”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已被画家、评论家、甚至是书法家讨论了上千年。这个概念使中国画形成了自身的语境要求和审美标准,也正是这个概念构建了中国画的生命血脉及个性面貌,并终于使得中国画成为东方艺术形成的代表。
中国画的“笔墨”是中国画特有的规范化绘画语言,它有其自身的样式和要求,特别自谢赫提出“六法”以来,中国画家的有笔、有墨方式便被界定在一个有章可循的范围内,中国画家只有通过艰苦的历练才能掌握中规中矩的“笔墨”,也只有“有笔、有墨”的绘画才有幸被冠以“国画”的头衔,任何无视“法度”的所谓个性化“笔触”都是注定要胎死腹中的。由此,便有人把“笔墨”当成了束缚中国画发展的腐朽的东西。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正是由于“笔墨”要求的存在,才避免中国画堕入当下西画的尴尬处境。关于“笔墨”之讨论由来已久,对其顶礼膜拜者有之,对其耿耿于怀者亦不在少数。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不管你喜欢与否,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不会因为几个人短短几十年的对抗而消亡的,割裂中国文化的传统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所以,我们也只有谦虚地面对传统,并以赤子之心对其进行严肃的梳理与解读。
田:当下,许多艺术家都往北京等一些大的城市或海外跑,你把自己的艺术会所放在淄博的初衷是什么?
曹:文化精神上的回归,离中国越远,越深刻体会到齐鲁文化的厚重。
书画艺术在淄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在淄博有自己的艺术活动空间,是每一位艺术家的共同梦想。
同时,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为有探索意识的艺术家架构起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相信不远的将来,这里将会成为国内、国际艺术家的汇集之地,为淄博的文化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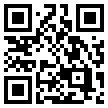
曹俊 微官网
请保存,可以印刷到名片或画册